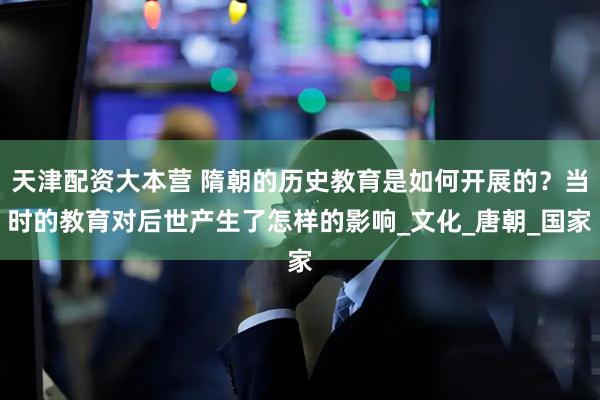公元826年冬,一对同年出生、惺惺相惜的诗人初遇在扬州的一座酒楼。二人正是刘禹锡和白居易。刘禹锡经历的沦落光阴,让白居易十分同情。白居易吟道:“亦知合被才名折,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刘禹锡随即回道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这场相逢牛达人,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词云:“叹人生、不如意事,十常八九。”刘禹锡的一生有太多不如意,甚至被网友称为创造了“唐朝官员史上最长的贬谪纪录”。然而他从未被命运击垮,还因乐观豁达的诗风被称作“诗豪”。即使在千年之后,刘禹锡依然是网友们推崇的“好心态”偶像,有道是:“人生若觉不如意,劝君多读刘禹锡。”
刘禹锡,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,清顾沅撰,孔继尧绘 图源:“北京大学出版社”微信公众号
一
公元772年,刘禹锡出生于嘉兴。父亲刘绪是“朋友圈”里有名的“鸡娃”家长,青少年时期,刘禹锡就颇具才名,之后又去长安进修,认识了柳宗元等同学。二十出头,他一举考中进士,之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、吏部取士科,三年之内“三登文科”。
展开剩余81%在那个“五十岁考中进士都还算年轻”的时代,刘禹锡实属英才。“又被时人写姓名,春风引路入京城”,在他的诗中,也洋溢着一丝小骄傲。
怀揣着中兴朝廷的壮志,他还参与了“永贞革新”。然而,失败接踵而至,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,刚过而立之年,刘禹锡就踏上了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的被贬之路。
朗州是刘禹锡被贬的第一站。在这偏远之地,刘禹锡生活了十年时间。困顿失意时,他很懂得调节自己,流连山水、“指事成歌诗”,在风物之中寻求治愈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著名的《秋词》便诞生于此。
离开朗州后,刘禹锡曾被召回长安,却因一句“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”惹怒朝廷,被贬至连州,之后又被贬至夔州、和州等地。
一路颠沛流离,治愈刘禹锡的不仅有山川之美、淳朴民情,还有一件件为民实事。他在《连州刺史厅壁记》中写道“功利存乎人民”,并歌颂四位前任连州刺史功绩,有意追随他们的脚步。除了修水利、兴教育等实事,在连州时,刘禹锡还差人搜集民间药方,又写信给柳宗元等友人求助,最终编成《传信方》,治好了当时频发的“呕泄之患”。
不管是在京城力主改革,还是在基层办好实事,乐观的刘禹锡无论在哪都能找到自己的事业。人生如逆旅,谁都免不了磕磕绊绊,重要的是不易其心、不移其志。正是这种人格魅力牛达人,让“刘禹锡”常读常新。
刘禹锡雕塑位于嘉兴市区环城河绿带秀城桥南侧 图源:“读嘉新闻”微信公众号
二
谈及刘禹锡屡次被贬的经历,白居易惋惜不已。同样的遭遇,若是换个心态不好的人,估计早已不遇而终。那么,刘禹锡究竟凭借怎样的“好心态”穿越人生的风浪?
不内耗。在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中,刘禹锡也不是没有烦闷的时候。比如,刚到连州时,每每想起政敌的谗言诬告,刘禹锡就心气不顺。但直率的他不会把愁苦的情绪憋在心里,总能找个机会抒发出来。当他听闻与自己不合的宰相武元衡被暗杀的消息后,心情复杂,但还是借机写了几首讽刺诗,把被佞臣诬陷、遭政敌猜疑的愤恨发泄了一通。
不在意。“命压人头”,刘禹锡则随遇而安。他当官不摆官架子,喜欢去民间采风,根据民歌、民俗创作了不少风情俊爽的诗文,如《采菱行》《竞渡曲》等,还有独具特色的“竹枝词”诗体。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,能写出这般句子的诗人,想必不会囿于贬谪之困。
远离宦官和朋党争权夺利的游戏,他更不在意那些朝廷的流言蜚语。他还经常劝慰柳宗元,并引荐朋友给对方。有学者认为,柳宗元能创作出著名的《永州八记》就离不开刘禹锡的勉励。
不计较。被网友戏称为“大唐直男”的刘禹锡,其实是通情达理的。他不会以个人的好恶来看待人和事,而是能够跳出非黑即白的对立框架,看到一个人身上的复杂性与时代的局限性。
比如,在被贬为朗州司马时,曾经的对头窦群突然造访。听完窦群的贬谪经历后,刘禹锡不仅没有半分嘲笑,反倒不计前嫌,以“贬谪过来人”的身份安慰起了这位政敌,还答应对方请求,帮忙代撰谢表。
“好心态决定好状态”。纵观刘禹锡的一生,他的乐观似乎刻在了骨子里。有网友说:“他像一个太阳,影响着身边的人。”不仅是柳宗元,还有韩愈、白居易、元稹等,就连苏轼也是刘禹锡的异世知己。“看取桃花春二月,争开。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这正是苏轼对偶像的“告白”。
刘禹锡诗云: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”图源:“北京大学出版社”微信公众号
三
积极乐观的刘禹锡,也曾为人生无常“惊号大哭,如得狂病”。公元819年,年近半百的他刚经历与母亲的生死离别,却又接到了挚友柳宗元离世的噩耗。
一时之间,悲恸夹杂着惊惧涌上心头,刘禹锡痛哭流涕,久久不能平复。后来,他在《祭柳员外文》中写道:“呜呼子厚!卿真死矣!终我此生,无相见矣。”
这大概是刘禹锡人生的至暗时刻。妻子与母亲相继离世,至交好友又溘然长逝,回京的希望仍十分渺茫,这样的日子该如何过下去?
沉寂许久之后,柳宗元的一纸遗书让刘禹锡想通了——他要为逝去的人活下去,更要为活着的人活下去。他的孩子,还有柳宗元托付给他的遗孤和有待整理的遗作,都等着他重新打起精神来。
有人评价刘禹锡,似乎什么都不能打倒他,政敌不能、贬谪不能、衰老不能,就连死亡也不能。当年过七旬的刘禹锡来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拖着虚弱的病躯,为自己写完了最后一篇文章——《子刘子自传》。
“不夭不贱,天之祺兮。重屯累厄,数之奇兮。天与所长,不使施兮。人或加讪,心无疵兮。”他在文章里告诉世人,老天赐予我才能,却不让我施展,即使小人诽谤,我心中也永怀光明、不存阴影。
刘禹锡不是标签式的人物。当代年轻人喜欢他,或许是学习他落寞时的从容沉着,或许是欣赏他“莫道桑榆晚”从不认命的硬骨头,或许是钦佩他逆境中坚守“民生为念”的情怀,还有他一次次走出至暗时刻的生命张力。
有作家评价刘禹锡起落悲欣的一生:“人生的困顿也许很长,但终究长不过人世间的希望与温情,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有挣扎与落寞。”千古风流人物不计其数,但像刘禹锡这样的人依然难得。在感到失意沮丧时,不妨多读读刘禹锡,相信总有那么一个瞬间,会给予你千帆过尽、翻篇出发的力量。
本文播音:韩欣阅
声明:稿件未经授权牛达人,不得转载。
发布于:北京市汇盈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